资讯分类
千呼万唤,又见林青霞 -
来源:爱看影院iktv8人气:219更新:2025-09-09 14:5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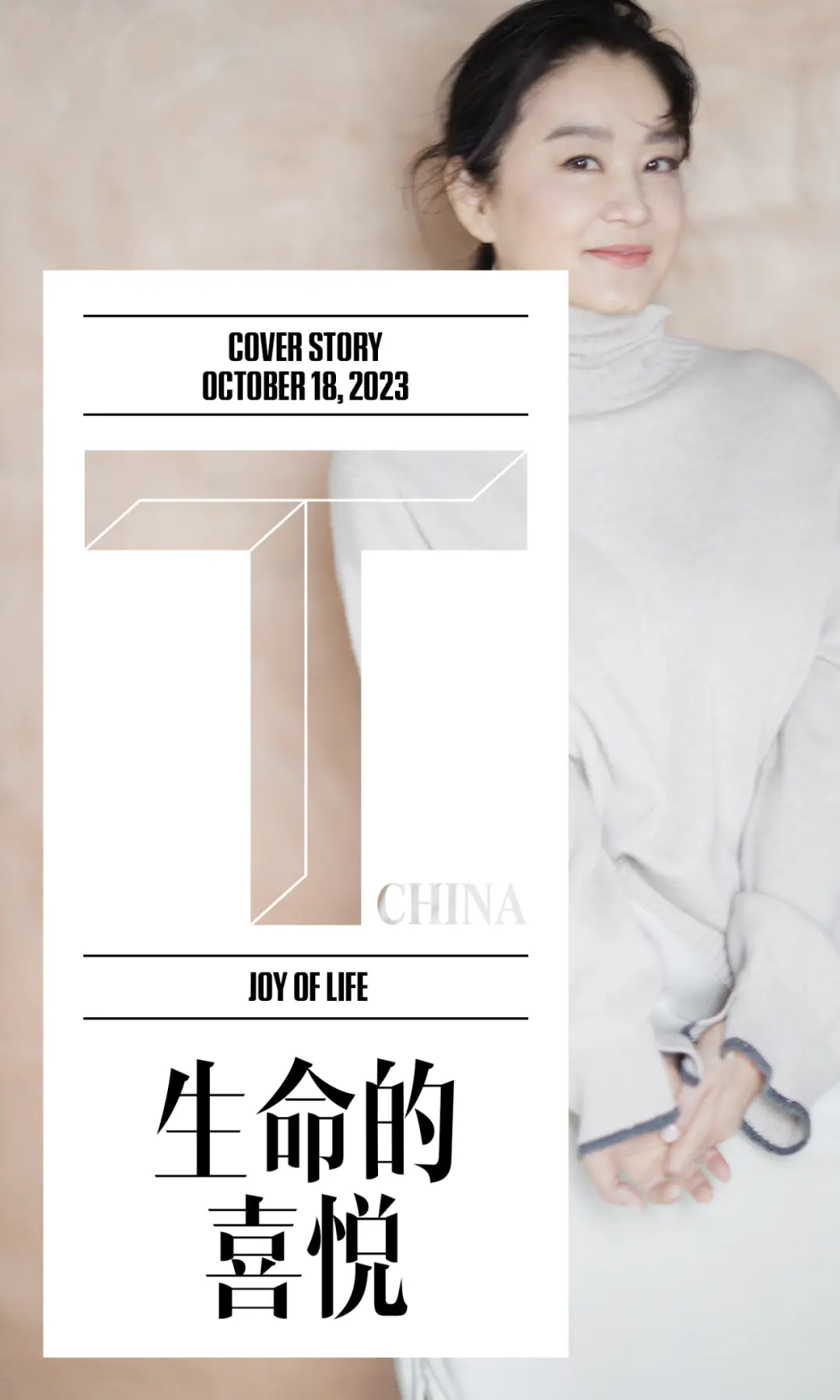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的内搭、西装、半裙、手帕与丝袜,与Cartier白金、红宝石、钻石打造的高级珠宝耳环及项链共同构成了林青霞的时尚叙事。这位资深演员曾坦言,生活中唯一接触过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是她的婆婆——一位年仅60余岁的长者,恰与林青霞当下的年龄相仿。确诊后的婆婆常常陷入记忆的迷雾,不仅会忘记物品的摆放位置,更会展现出多疑与情绪失控的特质。在医院的陌生环境中,护理人员常需以善意的谎言安抚她的情绪,如告知其「这是我们家抽奖送的酒店」,方能让她暂时安顿下来。然而,这种短暂的平静终将被持续的混乱取代,患者的意识如同被冰封的河流,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当林青霞从八本Ernaux作品中翻出《一个女人的故事》时,她不禁联想到法国作家Annie Ernaux笔下母亲的病态人生。Ernaux的母亲同样饱受阿尔兹海默病困扰,其在书中描述的「生活在一种不耐烦之中,无限的不耐烦」与「全部的情感只剩下愤怒和怀疑」,恰如其分地映射了病患者的生存状态。在极少数清醒时刻,病人试图给友人写信,却只能在信笺上留下「亲爱的保莱特,我怎么也不能走出我的黑夜」这样破碎的句子。这个深秋的傍晚,林青霞刚结束两小时的试装与试拍,当众多工作人员散去后,她独自走到昏暗的墙角,选择一条黑色沙发静坐。身着宽松白衬衫与深色贴身牛仔裤,清瘦修长的身形在斜靠时更显从容,手背支着下颌的沉思姿态,恰似她收藏的常玉后期人物画作,以简洁的轮廓与润畅的线条,勾勒出某种永恒的诗意。

林青霞近年来陆续观看了多部聚焦阿尔兹海默病题材的影视作品与文学创作。在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2020)终场戏中,耄耋老人因孩童般脆弱的情绪流露而令人心生共鸣——"我感觉我的叶子都掉光了",这番台词触动了她感性的一面。而对疾病医学层面的认知,则源于去年圣诞节的一次特别对话。当时她与医生赵夏瀛、文学教授金圣华在半岛酒店共进下午茶,听闻"脑退化症项目"的相关数据:全球约有5500万患者,但仅78%的人了解其临床前期阶段,且仅有17%选择接受专业诊疗。与此同时,中国香港作为全球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女性平均寿命达87岁,男性则为81岁。作为京剧爱好者,林青霞曾与同为巨星的葛兰共同参与票友活动,7位参与者中有3位超过90岁。68岁的她虽属年轻一代,却依然可以展现撒娇逗趣的"小朋友"特质。在一次票友聚会中,她目睹一位99岁高龄的参与者,无需拐杖或轮椅,在西装笔挺的状态下独自前来。三位逾90岁的票友仍能保持中气十足的唱腔,交谈时毫无顾忌,这种潇洒自在的晚年生活显然无法用"老先生"或"老太太"来定义。当日众人共享欢乐时光,临别时玩笑般提议将90岁的葛兰与99岁的票友组合成一对,林青霞忍俊不禁地举起相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这般活泼的场景,与5500万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不同生命状态的差异。

林青霞身着Brunello Cucinelli针织衫,在半岛酒店积极投身于「脑退化症项目」的推进工作。她主动与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院长莫仲棠、脑神经科专家以及高锟慈善基金主席黄美芸达成合作共识,共同推动该公益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她与中文大学的因缘始于二十多年前的一场颁奖典礼,彼时她的丈夫邢李㷧与善衡书院前院长辛世文同获殊荣,辛世文在致辞中曾表示对林青霞影视作品的喜爱,称其为「影迷」。此后十余年,2018年林青霞更获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授予荣誉院士名衔,这一荣誉在当下充满争议的网络环境下仍获得广泛认可,既源于她个人的成就,也印证了与大学之间深厚的善缘。
作为佛教信徒,林青霞曾前往印度新德里参拜大宝法王,并在中国台湾法鼓山跟随圣严法师修习禅法。佛家所言「结善缘」,正是她近年来践行的理念。正如她今年春天在社交媒体上所言:「我将竭尽所能奉献出最好的自己,积极参与对社会有益的事务。」
2023年9月21日,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当天,香港中文大学利希慎音乐厅见证「高锟中大『脑智同护』服务」正式启动。活动上,林青霞以5分钟演讲分享生活感悟,着淡蓝色羊皮外套、白色长裤与低跟皮鞋,展现出优雅亲切的气质。这位即将年满69岁的女士步履轻盈,神采奕奕,与佩戴的镶钻豹形戒指交相辉映,彰显出她对生命热情的掌控。她谈及:「今年我68岁,11月将满69岁,我的记忆力与反应力相较60岁前更佳。通过阅读、写作、绘画、戏剧,参与正能量社交,保持规律运动,我仿佛过着全新的人生。这些都能成为对抗脑退化的良方,若以60岁为起点重置人生,我如今不过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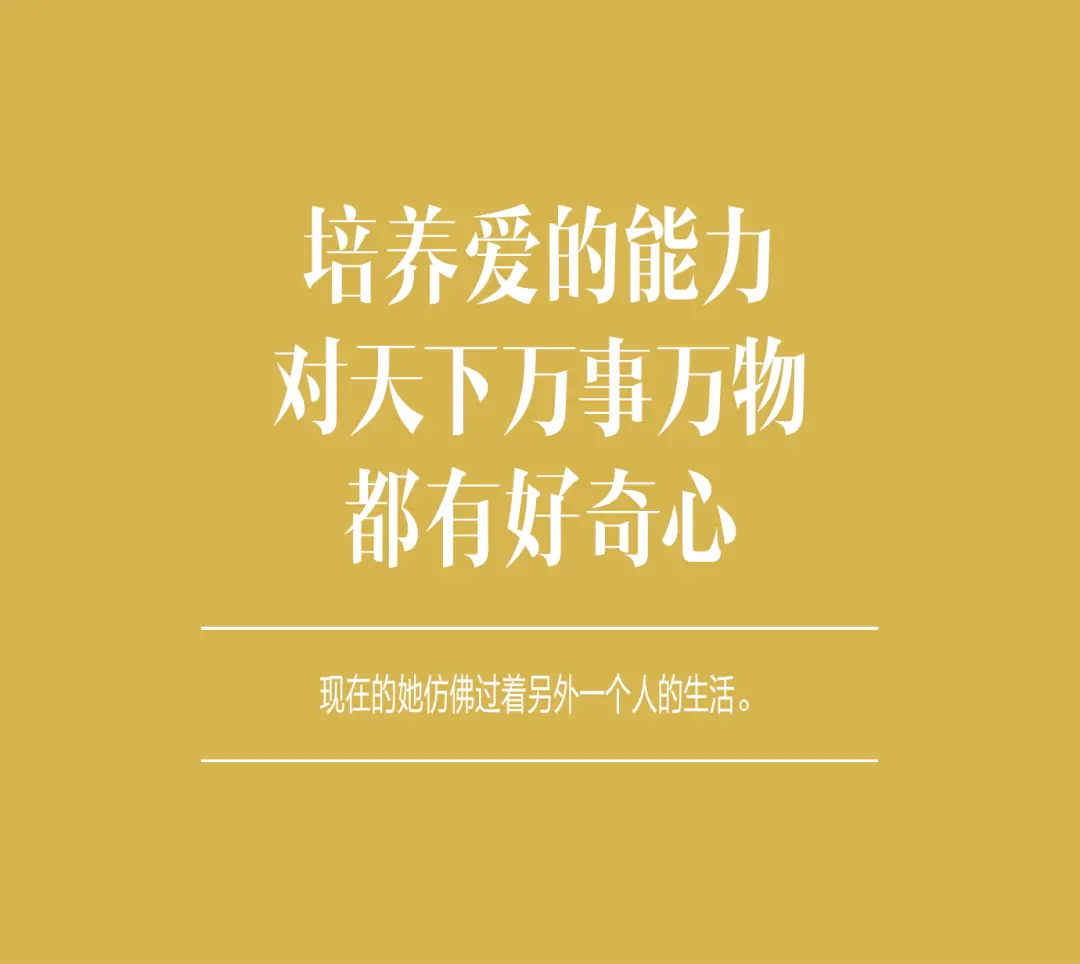
她放下话头,肩头微微一耸,嘴角浮起一丝俏皮的笑意。满堂喝彩与经久不息的掌声,印证了她的艺术才华与感染力并未因淡出影视圈而消退。她轻声细语地分享着与高龄挚友共度的欢愉时光。尽管大众早已见证过她辉煌的演艺生涯,但当她以生活本真的姿态现身,却仍让人感受到‘有些人始终活在黄金时代’的神奇,以及‘人生或许可以永远处于黄金时代’的想象。深夜研读Ernaux作品、静默凝视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婆婆,那些深沉的情绪与混沌的记忆,她选择将其隐匿于暗夜之中。她期待每一次公开亮相,都能为众人带来新的感动,注入生命的活力。正如她对世人坦诚分享的感悟:‘相较于过往,此刻的生命或许更加从容、喜悦与自由。’
林青霞的‘晨间’始于午后三时。身为夜猫子,她延续着年轻时的作息,彻夜不眠。日常起居大致如下:午后三时起床,以玉米、红薯与水煮蛋等简朴餐食开启新一天。随后便前往太平山快走两圈,耗时八十分钟,直至额角沁出汗珠。若遇阴雨天气,则选择在家练习普拉提,并邀请友人来茶叙聊天。挚友金圣华曾提到,她们的对话多半围绕书艺创作与文化圈动态,仅三分之一用于闲聊,诸如家庭、服饰与日常琐事等话题。若有余暇,她会走进街巷闲逛,选购心仪之物。晚间则以乒乓球为乐,几乎每日坚持。
2020年冬,《镜前镜后》散文集付梓,出版社需五千余本亲笔签名,为避免右手疲劳,她熟练掌握了左手击球技巧。对这项运动的热情让她沉醉其中,不知不觉便踏入深夜。午夜时分,众人沉睡,她则独享属于自己的时光——自零时起,步入书房,书桌前静坐。这一时段专属于她,是她生活的核心:绘画、书写与阅读。多番尝试后,执笔创作常持续六至八小时,仅在如厕时短暂起身。清晨六时,她即能感知天色渐亮,这源于她对时间的敏锐。待天色微明,她便开始洗漱整理,随后安然入眠。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的上衣与手镯在四周静谧中若隐若现,而她内心的火焰却悄然燃烧——不似燎原之势,更像是壁炉里跃动的火苗,轻柔地舔舐着松木,既缠绵又执着。这份创作的热忱,或许源自她2011年出版的首部作品《窗里窗外》,又或更早可追溯至2004年发表于《明报》的纪念黄霑专栏《沧海一声笑》。她偏爱执笔于稿纸,将文字逐字凝结,「写得不顺时便将稿纸揉作一团掷于地面,散落满地的纸团仿佛上世纪电影里潦倒作家的写照,带着几分戏剧张力。」当创作欲望最为炽热时,她曾这般描述:「某日归家后途经梳妆台,灵感倏然而至,生怕遗忘便俯身疾书,竟在桌前坐了数小时。待到窗外传来鸟鸣方知天已破晓,照镜时才发现妆容未卸,钻石耳环仍在轻晃,身着蓝色丝质褶裙与高筒靴,时钟指向六点半——正是女儿晨起进食的时辰,便匆匆下楼陪伴。」作家董桥曾赞誉其文风「叙述质朴直接,文字清澈明晰,仅用十六个逗号勾勒出深夜伏案写作的全过程,疏而不散,尽显功力」。林青霞自十八岁踏入演艺圈,参演百余部电影,成就无可争议的巨星地位;四十岁婚后息影,于文集中自嘲「嫁作商人妇」,转型为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过上了寂寂无声的日子。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她重拾笔墨,成为横跨内地、香港、台湾与新加坡报刊的作家,出版四部作品。她的文字如同人生轨迹般独特,正如白先勇所言:「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于前半生在演艺圈驰骋二十载,结识的皆是璀璨星辰。」当张国荣离世的消息传来,她悲痛欲绝,既自责又质问公司「为何未为他安排医生」。在处女作《窗里窗外》中,她回忆起一九九三年与他共同拍摄《东邪西毒》与《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的日子,那时他们同住湾仔的会景阁公寓,常乘公司小巴前往片场。某次乘车途中,他询问她的近况,她语未竟便泪如雨下,沉默片刻后,他轻抚她的肩头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两人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某日,她身着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的上衣与手镯,前往文华酒店与友人共度下午茶时光。她有意避开位于二层的克利伯休息室长廊,因那承载着张国荣当年发生不幸的事。然而当天,她神思恍惚,仿佛脑内分岔出两条轨道——一条自动应答着友人闲谈,另一条却不断穿梭回过往的片段。
据她在《云去云来》第三本书中所述:「我竭力集中注意力,却总浮现国荣曾在此与我对面相谈的话语:『青霞,别再频繁拍戏,也少打些麻将……』」她坦言并非有意成为作家,却意外走上创作之路——文学的规律同样适用于她,其间还交织着一段渴望知识的漫长读者生涯,这正是她踏入文学领域的学徒阶段。
金圣华提及,五六年前提及林青霞曾与她频繁探讨的作家包括契诃夫、太宰治、毛姆、海明威、杜拉斯、昆德拉、阎连科与马尔克斯等。林青霞以求知若渴的热情,广泛涉猎经典文学作品,常常产生独特的感悟,例如曾言:「若非卡夫卡患有抑郁症,他恐难以写出《变形记》这般作品,其内心挣扎我感同身受。」
与此同时,她积极寻求文学导师,广结作家朋友,曾亲自拜访季羡林、杨绛、黄永玉,赴台湾大学聆听白先勇解析《红楼梦》。其书房更成为文化名流的聚集地,不久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到访,因祖籍山东,两人自然以乡音交谈。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的服饰、披肩与配饰伴随林青霞度过了漫长岁月,沉淀出如星辰般闪耀的回忆。与作家王安忆初识时,她收到一本以个人照片为封面的笔记本作为礼物;第二次会面,王安忆在笔记本内页写满小说手稿后郑重回赠。谈及这段经历,林青霞仍难掩感动:"王安忆真有心!我翻看时惊讶地说,你的眼睛是不是很好?字小得几乎难以辨认,像木心在监狱里缺纸时写的字。她解释说因为笔记本方格细密,所以字写得格外紧凑。这竟是她首次赠送手稿给我,相较之下,董桥曾多次索取却始终未予。"如今,林青霞最为推崇具备深刻自省力的文学创作者。他们以非凡勇气探索人性深渊,同时兼具卓越的表达能力。提及太宰治,她形容:"那份深刻的自我剖析让人揪心。"谈到Ernaux,则评价:"她的文字完美融合文学性、社会性与历史性,实属难得。"她更盛赞Orhan Pamuk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üzesi,2008)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1967),认为这两部作品结构严谨、意象丰富,展现出非凡的智性光辉。

林青霞正在创作的第五部著作聚焦于母女情深,书中描绘的母亲因长期遭受忧郁症困扰,最终离世。她在梦中常与离世的母亲相见,形容其"始终笼罩在阴霾之下,神情黯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注定充满挑战,作为文学中最为复杂的母题之一,母女关系的微妙层次需要二十年的沉淀与打磨。林青霞坦言,她希望将母亲还原为真实的个体,同时"勾勒出母亲渴望拥有的人生轨迹",这种创作冲动与情感执念,正如她所推崇的Ernaux所言:"此刻书写母亲,恰似赋予她第二次生命。"每当创作受阻时,她会幻想着成书后的装帧设计,如同母亲在孕育期间对胎儿容貌的憧憬,这种想象成为支撑她前行的精神支柱。她特别构思了以手绘插图替代传统照片的方案,认为"文字难以抵达的维度,应当由绘画来诠释"。

林青霞对欣赏之人总是怀揣着炽热的情感。面对喜爱的作家,她习惯性地以「通读」方式深入阅读;若这位作家亦涉足绘画领域,她便会兴致盎然地临摹其全部画作。这种情感在她对张爱玲的追随中尤为鲜明——尽管张爱玲曾坦言自己的小说中「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林青霞却展现出截然相反的特质,性格中蕴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彻底性。1990年,她主演的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滚滚红尘》斩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三十年后,在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张爱玲的著作、信件、访谈记录与学术评论摆放在床头,彻夜未眠地研读。据与她一同研究张爱玲的学者黄心村回忆,二人曾一同登山,站在山顶远眺香港的云海时,关于张爱玲的琐碎故事总会在交谈中浮现。彼时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曾居住在她们活动范围内的半山宿舍,林青霞时常凝视着快速掠过的云影,轻声自语:「若张爱玲看到这般景象,又会以怎样的笔触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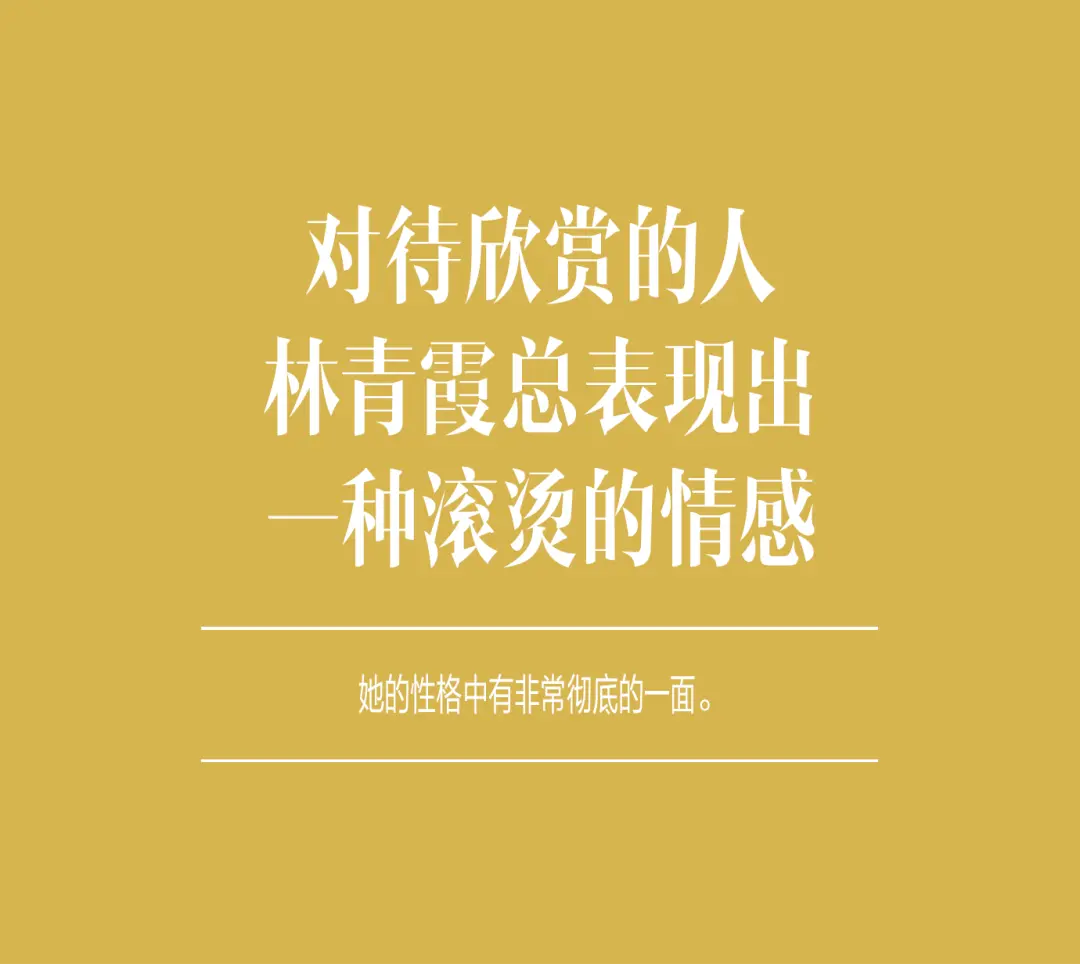
她对张爱玲精炼且锋利的文风有着深刻理解。1944年,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往往关注人生璀璨的表象,却忽略了人生安稳的本质。实际上,正是这种本质支撑着璀璨的呈现…… 缺少根基,璀璨不过浮光掠影。」当下的林青霞,已拥有远超张爱玲晚年人生安稳的境遇。然而,她仍不禁思考——「她是否仍会频繁登临精神的高峰?」2020年深秋,林青霞历经十余次修改,在《中国时报》刊发整版探讨张爱玲的专题文章,无意间展现了她数十年如一日研读的执着。文中提及,1981年于旧金山期间,专营张爱玲著作的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曾试图与她会面,却遭婉拒。彼时的张爱玲几乎每周迁居一次,辗转多处汽车旅馆,因皮肤病需持续照射日光灯达十三小时,每半小时需用清水清洁眼疾引发的异物感,面部药膏被冲刷后亦需不断补涂,如此反复竟耗费全天二十三小时于日光灯下。林青霞直觉认为这或是某种精神层面的病态,毕竟难以想象频繁更换居所仍会滋生虱子,眼部亦不会出现寄生虫。她随即致电精神科医生李诚求证,李诚推测可能是惊恐症伴随身体幻觉,严重时会产生皮肤爬行的错觉。林青霞追问:「这是否意味着真实并无虫害?」医生回应确认,但指出此症状可通过专业治疗得以缓解。

林青霞对张爱玲的执着追求贯穿其艺术生涯,这种精神认同超越了简单的偶像崇拜。近年来,她持续临摹张爱玲的画作,仅一年便完成整本素描册。在与漫画家李志清的结缘中,既源于偶然——她曾在朋友背上发现李志清的单线画作,赞叹其线条张力;也因必然——李志清从林青霞签名的笔迹中预见其绘画天赋。每周六的课堂上,她以白衬衫为装束,如同谦逊的学生般认真研习。谈及创作理念时,她坦言:"我平生无大志,只希望勤能补拙。"面对同一幅画作,他人耗时两小时,她却坚持十小时的投入。林青霞坚信艺术创作的相通性,认为写作与绘画能相辅相成。目前,她正以每日临摹五幅大师画作的节奏进行自我淬炼。当谈到法国野兽派代表马蒂斯时,她眼中闪烁着激情,特别欣赏其色彩运用与线条韵律。去年为深入研习,她收集市面上所有马蒂斯画册(共计三十本),连续昼夜作画,展现出对艺术纯粹的追求。

两个月前,林青霞身着Maison Margiela的衬衫裤装与球鞋,专程飞往东京参观马蒂斯艺术特展。此次展览由拥有全球最多马蒂斯藏品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协力呈现,除经典画作外,还汇集了雕塑、素描、版画及剪纸等多元艺术形式。「观展两日,他的画作传递出令人安心的宁静感,仿佛置身沙发放松身心。」林青霞坦言仍意犹未尽。这印证了马蒂斯百年前的艺术主张:「我渴望创造一种平衡、纯粹的艺术——它不应令人不安或困惑,让疲惫的人们能在画前重新获得平静与安宁。」展览的150件作品中,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绿线》(La raie verte),这幅更广为人知的《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画像》以克制的色彩构建画面,人物神情沉稳庄重。画中面部的绿色条纹既暗示光影层次,又规避了强烈对比带来的视觉冲击。林青霞返港后随即投入临摹,「那日风雨大作,司机无法出行,我彻夜作画,从起身到入眠持续十几个小时,仅中途如厕一次。翌日醒来继续创作,仿佛与画作融为一体。」这种近乎偏执的创作态度,恰与晚年马蒂斯的坚持相呼应——在经历十二指肠癌手术及两次肺栓塞后,他仅能以轮椅和床榻为画室,却始终保持着「五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节奏,从清晨九点持续至午间,午休后再度投入创作直至夜深」的创作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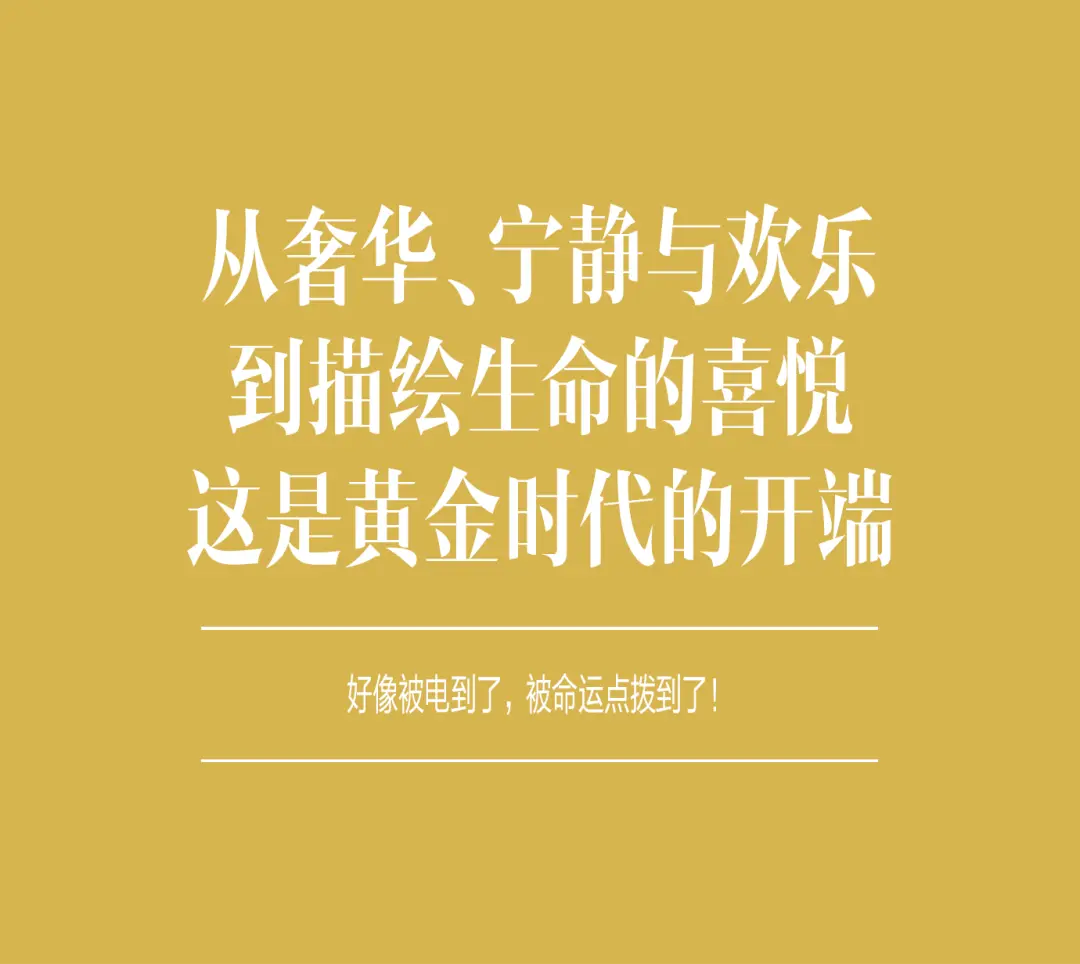
颇具意味的是,1905年马蒂斯在完成这幅肖像画之后,重新借鉴早期杰作《奢华、宁静与欢乐》的画风,创作出《田园》(La Pastorale),以此诠释「生命的喜悦」这一核心主题。这幅作品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点。次年,马蒂斯在独立沙龙展出《生命的喜悦》(Le bonheur de vivre),其充满张力的鲜艳色彩与自由奔放的笔触颠覆了传统「田园牧歌」的审美预期,引发激烈争论;然而对马蒂斯而言,这正是其创作黄金时代的开端。
某夜,林青霞邀约十二位挚友至半山书房共进宵夜。依照待客礼节,她于餐桌旁即兴挥毫,勾勒出这群友人的形象作为手绘礼物。待众人散去后,她忽然忆起马蒂斯。彼时其家族「大屋」遭遇火灾,所有典藏书籍被迁至半山书房暂存。她在地板上逐页翻阅马蒂斯的画册,沉浸其中直至末页最后一行,惊愕地发现画册末页记录着马蒂斯于1954年11月3日心脏停止跳动。而同年、同月、同日,林青霞恰好在中国台湾诞生。
最新资讯
- • 于冬亮相金巧巧新片首映 指导宣发策略谈及王宝强 -
- • 芭比》北美票房超《蝙蝠侠》 全球破13亿 -
- • 《音乐大师》发布预告 聚焦作曲家伯恩斯坦 -
- • 丹尼斯·维伦纽瓦透露《沙丘3》的剧本已经写好了 -
- • 重启版《毒魔复仇》电影曝剧照 奇幻电影节首映 -
- • 《威尼斯惊魂夜》发布特辑 寻找线索和真相 -
- • 喜剧片《梦想情景》定档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 -
- • 《星条红与皇室蓝》发布特辑 同性之恋状况不断 -
- • 《惊奇队长2》发布新剧照 酷飒反派来势汹汹 -
- • DC不计划开发《神奇女侠3》 前传剧集仍有戏 -
- • 《伸冤人3》发布特辑 特工大叔回归伸张正义 -
- • 《母性本能》发布预告 劳模姐海瑟薇演闺蜜 -
- • 《孤注一掷》密钥延期至10月7日 累计票房33.84亿 -
- • 《阿索卡》发布新海报 新老角色共谱传奇 -
- • 《早间新闻》第三季发正式预告 改编迫在眉睫 -
- • 《荒野》发布先导预告 出轨引发连环报复 -
- • 《就像那样》续订第三季 欲望都市故事继续 -
- • 《海贼王》真人剧集发新海报 少年冒险启航 -
- • 《美国恐怖故事》发预告 罗伯茨卡戴珊主演 -
- • 《波西·杰克逊》发布新预告 定档12月开播 -